
数据显示,大多发病率极低,诊治极难的罕见疾病的罪魁祸首正是基因缺陷。而这些缺憾在日后会逐渐凸显,从婴儿到幼儿、儿童、少年、成年甚至老年。
为修正“上天”的错误,有这么一群白衣战士走上一条“罕见之路”,倾尽青春和热血在这片无尽的探索途中,在浩瀚如海的数据中挖掘出点点生命的希望。在第二届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我们谨以此文诚挚地和这群勇敢的战士们说声:感谢有你!
23岁那年,我第一次意识到,疾病和死亡竟然可以离得那么近。
那是在瑞金医院ICU病房的度过一周,对面躺着一个很年轻的姑娘。我从来没见她起来过,基本一整天都是躺着发呆,直到被母亲扶起来吃饭时我才注意到,姑娘的脸看起来非常年轻却异常浮肿,身体呈现不成比例的肥胖,如同一个肿胀的梨。手似乎有些乏力,要靠着母亲把食物送入口中。
“姑娘才上大一,是典型多发性硬化。直到二次复发,周转了一年多才在这里确诊,可惜腿已经不能走路了。家境也不好,主任就帮着申请了干扰素的补贴,可惜现在都用完了,目前只能靠糖皮质激素维持。”护士悄悄说。
这样的情况无法不让人唏嘘。每天早上,主治医生都先来病房看她陪她说会话,和她父亲交流治疗方案,也陪着安慰哭泣的母亲。“再难我们都一起想办法,姑娘还小,咱们别轻易放弃。”这是离开前印在我脑海里最后的话。
多年后我做罕见病公益时,时常接触到一些残忍的数据。去年发布的《2018中国罕见病调研报告》显示,在专业的医生当中,仅有三成知道罕见病,坚持在罕见病一线研究的人员更是寥寥无几。这种情况下,病人均需要花费5.3年的时间才能被确诊,最极端病友历时44年才确诊。看到这一幕时我总会想起当时的场景:咱别轻易放弃。
“会看罕见病的医生比患者还要罕见。”上海罕见病防治基金会理事长李定国指出,罕见病领域的知名专家屈指可数,大部分罕见病患者的就医之路十分曲折,“每位罕见病患者平均要经过5~10位医生诊治后才能被确诊。”
“为什么能坚持这么多年耕耘在罕见疾病?”我问过每个采访者。
“第一次投入研究罕见病是从接到一个求助无门的母亲电话开始。此后,每竭尽全力挽留住一个孩子,就是对我最大的奖励。”一位从业20年的医生如是告知。
“中国至少要有一些医生
一眼能看出这个孩子出了什么问题”

沈亦平 “遗传咨询师”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医学遗传科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教委"东方学者讲座教授",
广西妇幼遗传代谢中心实验室技术主任,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神经系助理教授,
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遗传及基因组系医学遗传学培训班课程共同主任,
麻省总院基因组医学中心兼职研究员,
美国医学遗传学专家委员会委员。
2007年的一天,正在波士顿儿童医院研究基因诊断的沈亦平发起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寻人启事”。
他将当时人民日报上的一张“网红”的婴儿照片发给了国内的朋友:“帮我找找这个孩子吧,我想告诉他的主治医生,我知道怎么救他。”照片里的孩子有着一双肿大突出的眼睛和类似三叶草的头颅,上面有媒体夸张地印着标题:江西一村妇产下一名‘外星人’的男婴,在猎奇的头条栏目里被无数人传阅着。
这是当时国内大多医生闻所未闻的奇特病例,做了多年基因诊断的沈亦平却一下子看出了问题。“这是一种罕见的单基因遗传病(属颅缝早闭的一种),而不是什么‘外星人’。虽然看起来可怕,可如果能够在一岁以内做开颅手术,孩子在智力发育、独立生活等方面会和正常孩子一样;等再大一些做下整容,这个孩子很有机会恢复到正常的面貌。”
每次讲到这个故事,沈亦平都觉得遗憾,虽然最终他用尽了办法也没能找到这个孩子,但这却让他下定决心:以后每年都要回一次国,通过培养专业的中国临床遗传医师来帮帮这些可怜的孩子和家庭。
早在2008年时,遗传咨询在国内还是个很新的概念。尽管在美国它已经存在了30余年,发展了4000余名专业人士。可在我国,遗传咨询甚至都还没有起步,很多人为所未闻,更不用提足够的临床经验。既然眼前没有路,沈亦平愿意和国内的同道一起当起了这个开路人。

沈亦平医生
2017年,在见到那张婴儿照片的十年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遗传咨询师培训基地终于正式挂牌,同时《ACMG遗传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中文版也正式出炉,这个原本陌生的行业终于露出了曙光。不过,此时压在沈亦平及同行身上的责任更重了,未来要建立一个从培训到资格认证、到临床服务的“遗传咨询师”及能指导遗传咨询的基于中国病人的知识体系。
尽管“路漫漫其修远兮”,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沈亦平以此开始攀登人生的又一个险峰。因最初这个信念,沈亦平在波士顿接受了一百多个从全国各地到哈佛医学院波士顿儿童医院,麻省总院进修,有志于医学遗传与遗传咨询的学者,也每年为中国临床医生的医学遗传及遗传咨询开设了专门的培训班,同时积极参与中国遗传咨询分会的各级遗传咨询培训班。积水成海,积沙成塔,在沈亦平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加入这个挑战。
“中国至少要有一些医生一眼能看出这个孩子出了什么问题。”从背负起这个使命开始,不知不觉,不知不觉沈亦平已经在一线拓荒了20年。
“作为医生,理解患者和患者家属,
和治好他的病同样重要”

孙青芳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神经外科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沿着瑞金医院卢湾分院走到总院,一路挺立着原法租界独有的优雅的梧桐树。无数个晨钟暮鼓,行经的人都常看到孙青芳匆匆骑车而过。在第二季《人世间》中,第四集最后的镜头里就停留在这一幕,朴实的街景、蔽日的绿荫、和一位为库欣病人奔走的医生,组成了这个街头最寻常又最动人的一幕。

孙医生正骑着自行车来往于两院之间
几年前,为了让所有病人都能及时手术,瑞金医院将做过手术的病人安排到卢湾分院进行术后治疗,以便腾出床位给排队的病人做手术。为了帮库欣综合征病人争取好的术后管理,孙青芳“抢”了个分院的主任位置。此后,无论是上海夏日酷热的暴晒,还是冬日难忍的湿冷,一有手术孙青芳就得赶往总院,一旦病人呼叫又赶紧回分院照顾。借着卢湾分院的道路右边茂密的树荫,时间一久,她的右手比左手白很多,两只手伸出来,是截然不同的“黑白手。” 借用库欣秘书多年的MadelineStanton的形容,若把研究疾病作为从医者的“初恋,唯一的真爱”。孙青芳可为攻克库欣病这个“真爱””,付出了太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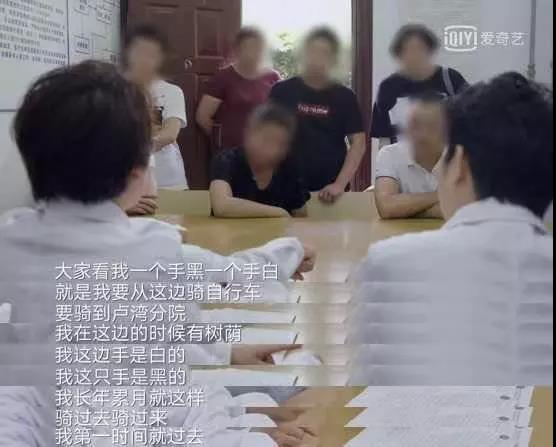
在棘手的罕见病中,库欣综合征是罕见中的罕见,发病率仅为5-6例/百万人。由于分泌过多的糖皮质激素,导致病人全身代谢紊乱,从发现至今,该病的诊断和治疗便成为困扰神经外科和内分泌科医师的一个世纪难题。如果不手术,50%的病人会在五年内自然死亡;可即使手术很成功,术后管理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激素过高不行,可忽然下降也是一个巨大的风险。
在这个特别艰难的“真爱”前,孙青芳坚守了30年。在神经外科这个男医生占多数的领域,孙青芳是第二位获得神经外科博士学位的女性,每天和大家一起钻研科研难题,挑战高难度、高体力强度的手术,每年平均参加手术200-250台。
和很多罕见病一样,库欣病多发于青壮年女性。在大量糖皮质激素的刺激下,患者多数会出现向心性肥胖,也就是说,脂肪大量地向脸部及躯干部胖集中,形成满月脸、水牛背、悬垂腹…… 这对于爱美的女性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可即使患者成功做个手术,安全度过术后危险的第一个月,也将面临一个异常痛苦的恢复过程——乏力、胃口不好、恶心、呕吐、蜕皮、脱发以及全身骨痛,这些症状会依次出现,逐渐加重,再慢慢缓解,逐渐消退,在这一过程中,超过一半的库欣病患者罹患重度抑郁、非典型抑郁和其他类型的精神心理异常。
理解是最好的安慰。孙青芳默默考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选择在这特殊时期陪伴病人。“作为医生,理解患者和患者家属,用较为专业的方法来处理其焦虑和担忧等问题,同样至关重要。”
带着这份初心,在医患矛盾经常冲击媒体头条的今天,用 “患难与共、同甘共苦” 形容孙青芳的医患关系竟然毫不违和,在病人最悲痛和最喜悦的时刻,她都守护在身边。
由于具有丰富垂体腺瘤的临床诊断和治疗经验,孙青芳不仅是库欣综合征患者的天使,也是重症孕妇的救治主力。2017年,她和科室同事接诊了两位患有脑垂体瘤并伴随出血的孕妇,结合多学科会诊、制定精密手术方案后,为患者摘除了肿瘤。术后不久,两位孕妇都顺利生下了宝宝,含泪给孩子起名为“瑞宁”和“瑞斌”,铭记在瑞金医院重获生机的经历。在这以后,多位脑出血患者的孕妇都慕名来瑞金生产。

高危产妇顺利产下了可爱的宝宝
在被她诊治的病人眼里,如果天使有具体的模样,那一定是孙青芳的样子。
在重大的灾难前,同情彰显我们的清白,爱却能创造奇迹。
所幸的是,在开始做公益的这些年,这条原本“罕见”的路上,已经看到越来越多的同行者。有发起慈善音乐会的中学生,有牵着孩子参加义卖的母亲,有放弃高薪工作全职投入公益的名校毕业生,把旁观变成行动,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在今年三月的国际罕见病日里,中国首部《罕见病诊疗指南(2019年版)》正式发布,为121种罕见病诊疗提供依据。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宣布,建立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以加强我国罕见病管理,提高罕见病诊疗水平。
“总有需要我们救的人。研究的人多了,看的案例多了,这原本万分之一,甚至百万分之一的希望也慢慢亮起来。”一位年轻医生说。
或许,这就是我们纵然有痛苦,但始终充满希望的人间。

本文作者/七色堇罕见病联盟
执行主编/尹学兵
值班编辑/赵青青


 有任何意见、建议、投稿,欢迎 发送到邮件sjyl1901@163.com
有任何意见、建议、投稿,欢迎 发送到邮件sjyl19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