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敏芳教授正坐在诊室,门被推开,抬头一看,原来是阿惠:“陶教授,今天我来再配点药。”陶教授示意请她坐在边上的椅子上候诊。正好刚接诊的患者起身离开。
陶教授上下打量了一眼阿惠,修剪整齐的短发,薄薄的羽绒服好像是新的,脸色红润,神清气爽的样子让她脱口而出:“您现在越来越精神了嘛!”
陶教授始终没有忘记两年前阿惠的样子。
那是她第一次接诊阿惠。当年阿惠是老公陪着她来自己的诊室。那时的阿惠头发凌乱,衣衫不整,尤其是颈脖子上围着两条毛巾,给她留下了邋邋遢遢的印象。老公让阿惠坐在陶教授面前,她发现阿惠的眼神是飘忽的。”您有什么不舒服?”陶教授问。于是,阿惠絮絮叨叨地说起了她的故事:
“我在2007年4月18日51岁的时候,在一家大医院开过刀,医生说我卵巢有囊肿,要拿掉,后来开刀的时候子宫也被拿掉了。我去问医生,她们说子宫里有肌瘤,一定要拿掉的。可是,4月30日我出院以后就觉得浑身痛,关节也痛,每个关节都痛,人没有力气,汗水很多很多,每天都要汗湿几件衣服,我准备了6条毛巾替换着用,贴在背上吸汗。汗多吧,应该是怕热,可是我就是怕风怕冷,就是觉得寒气从背脊上往下窜,大伏天里我要站在太阳下面晒,“孵太阳!”像过冬天似的。家里不能开冷空调,老公、儿子热得受不了。没办法,我就跑到我们家另一处房子自己一个人住,好在我们家有两套房子。
那是五楼,我常常坐在窗台上,耳边好像一直有个男人在说:你可以去死了,你可以去死了,好几次我就想把脚伸下去一跳算了,自己了结自己,这样活着真没有劲,可是我又想五楼不算高,跳下去不死怎么办?我心里郁闷啊,中药也吃了一年了,专家也看了好几位了,浑身难受怎么就看不好呢?我懒得和亲戚朋友来往,他们看到我大热天穿两用衫围毛巾都笑话我。只有我家钟点工阿姨会劝我,说我儿子马上要结婚了,老公又是市政府的公务员,多好的家庭啊,她说她都羡慕死了。
我觉得钟点工也不理解我的痛苦,我就跟老公“作”,不让老公碰我。就在我手术那天,医生把我切除的子宫、卵巢放在一个盘子里拿给老公看,血呼呼的把老公也吓到了,自从那以后,他对我也没了‘性趣’。
儿子要结婚了,老公和我骑车一起去定购新房装修的东西,我觉得耳边的风“呼啊呼啊”好大好大,问老公:“今天风好大噢?”老公回说:“今天哪有风?不要太热噢!”那天回家后我的头就非常非常痛,扎好围巾倒头就睡。从此后我更加怕风了,老觉得耳边有风声。老公让我散散心,和我一起遛狗狗,可是我的眼睛总是离开我的爱犬尼尼,我仰望天空,寻找周围的高楼,心里想着从哪一层楼跳下可以死掉,如果门卫不让我进去怎么办呢?如果跳下来不死骨折了要送医院,医院里都开空调的,我怎么办呢?我是最怕冷风的啊……每天我都在想怎么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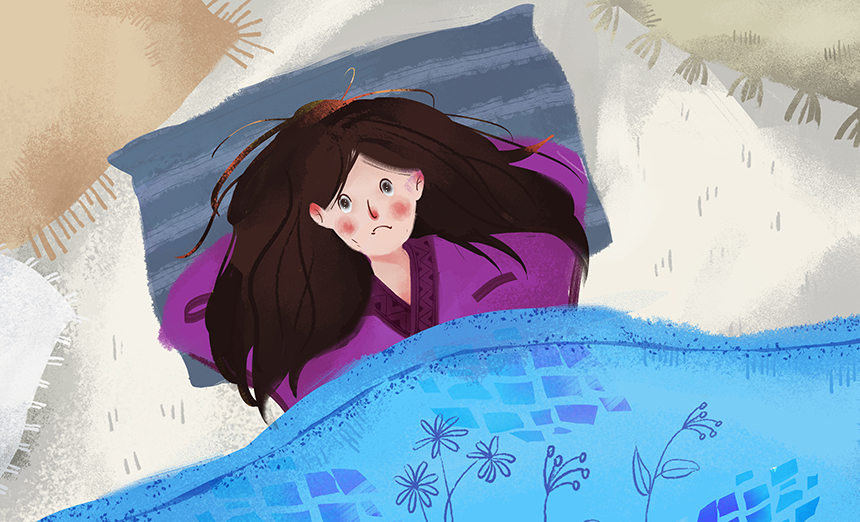
眼见阿惠唇干舌燥,语速变慢,陶教授接上她的话茬:“我们先帮你做些检查,根据你的症状和检查结果可以用些雌激素的药,症状一定会改善的。”“啊呀,雌激素用了会得癌的!”陶教授的话被阿惠打断。“你死都不怕,还怕癌!”站在一边一直沉默不语的阿惠老公突然说话。陶教授感激地对她笑了笑。
那天,阿惠接受了检查,诊断是明确的,她患上重度“更年期综合症”,陶教授为她开出药方,还推荐她到心理科叶建林副主任医师诊治。
一晃多年过去了。从存档的资料上看,阿惠的病情大有好转,“绝经指数评分表”显示其从首次测评的44,直到今天测评的15,这个客观数据也表明她的更年期综合症已是轻度了。反映阿惠主观感觉的“更年期评分量表”也记录着她从“19、25、15”降至今天的“6”。阿惠已经不再怕风怕冷,关节肌肉疼痛感消失,老公陪她去了海南、厦门、香港、澳门等地旅游,她融入了亲友的圈子生活恢复了常态。
像阿惠这样的患者,主要是因为子宫、卵巢的切除,造成体内雌激素水平骤然下降,而引发的“更年期综合征”。卵巢是女性的性腺,具有排卵的生殖功能和性激素的内分泌功能,卵巢切除术后引起的心理问题已经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子宫切除会影响内分泌功能的改变吗?答案是肯定的。每年全世界因各种原因行子宫全切术者约有65万。
子宫与卵巢间保持着精确而细微的内分泌动态平衡,从子宫动脉供给卵巢的血液占卵巢全部血供的50%~70%,切除子宫不仅破坏该平衡,且阻断了来自子宫方面的卵巢血液供应。另外,从社会心理角度分析,多数女性都认为子宫是保持女性特征和产生性感的唯一器官,因此子宫切除手术有别于一般的外科手术,会产生较明显的心理改变,这些心理问题甚至会影响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阿惠的例子就是明证。
因此,对于卵巢、子宫切除的患者雌激素替代疗法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
文/陶敏芳(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副院长,妇产科教授)
特邀通讯员/顾海鹰
值班编辑/孙雯


 有任何意见、建议、投稿,欢迎 发送到邮件sjyl1901@163.com
有任何意见、建议、投稿,欢迎 发送到邮件sjyl1901@163.com